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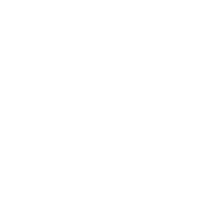
英国《金融时报》11月1日刊登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文章,题为“资本主义的大问题”。以下为文章主要内容。

为什么如此之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有4年多的时间,但直到现在,才兴起反资本主义抗议(抗议波及到了圣保罗大教堂)。那么,这是不是左翼政治复兴的开端呢?我对此表示怀疑。抗议者是否提出了一些重大问题?是的,的确如此。
这股浪潮要成为新左翼政治的开端,必须具备两个因素:第一,必须出现一种令人信服的新意识形态;第二,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背后必须存在着某种社会力量。
19世纪到20世纪初,新涌现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背后的力量则是有组织的工人。社会主义成功地建立起了福利国家。社会主义是一股保守力量,致力于捍卫一个多世纪以来逐步争取到的权利。另一方面,工人组织仅在公共部门确立起了牢固的地位。这赋予它同样的保守使命:维护福利国家。英国公共部门工人针对财政削减计划发起的罢工,就可说明这一点。
如果从传统左翼身上找不到答案,自由市场能够像往常一样立刻恢复运转吗?不能。相信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联姻的人士必须解决当前的事态。这首先是因为有一些更加阴暗的政治思想正蠢蠢欲动:国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当传统上层集团失败了、民众的失望情绪高涨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不能眼看着这种悲剧重演。
亲市场阵营应对危机的策略,大体上因循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套路。他们中有些人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于政府。美国的“茶党”便是如此,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在英国,这股势力比较弱,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场危机是戈登 布朗(Gordon Brown)在财政上恣意挥霍、政府对市场监管过度或央行无能等因素导致的。他们沿袭了上世纪3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格 冯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思想。与他们相对立的人士,则奉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张实行“有管理的资本主义”(managed capitalism)。
这场辩论主要又是围绕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应用:在衰退中应该收紧、还是放宽财政政策?在极端环境下,非常规货币政策是通往恶性通胀之路,还是有效的政策?正如上世纪30年代激进凯恩斯主义者的逐渐兴起一样,一个支持加强市场干预的派别也正粉墨登场。
这场辩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依我看,两种观点都有用。茶党关于未来政府角色的看法是错误的。即使是美国也不可能回到19世纪。但茶党中比较有头脑的人士则是对的(并且与当今的抗议者所见略同),他们认为,我们已经缔造了一种内幕人资本主义(an insider form of capitalism ),它利用、事实上也制造了补贴和税收上的漏洞,让内幕人士得以从中渔利、大发横财。不得不拯救银行这一点令人惊恐。金钱在政治中的角色令人不安。危险在于,我们正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 诺斯(Douglass North)所说的“开放介入秩序”走向它的对立面——这是一种政治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
这不仅是低效率的,也是不公正的。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妒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财富。但对于从接受纾困企业中涌现出来的富人,人们则抱着不一样的眼光。纾困必须到此为止。改革金融业使其能够取信于人,对于未来至关重要。但这还不够。市场资本主义造就了内在的困难,其中最明显的两种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和极端的不平等。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自我消耗的倾向再次隆重亮相。说起自由市场,右翼人士声称,如果我们回到金本位制、或者结束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度,那就万事大吉了。我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对未来进行押注,必然就会有不稳定性。人类的乐观和悲观思潮似乎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减轻不稳定性、缓解相关后果的方法从来都有待于寻找。
什么程度的不平等是可接受的?我们找不到标准。只要大家认为富人们是通过操纵、而非通过诚实竞争发家致富的,这样的不平等就是有害的。随着不平等的程度上升,公民人人平等的感觉就会淡化。最终,民主被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人。这是共和政体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和平抗议是自由公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抗议使问题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左翼不知如何取代市场。但亲市场者还是必须认真对待这些抗议。眼下并非事事顺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