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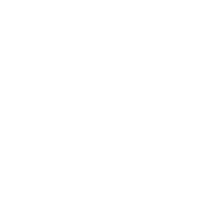

下乡务农的杨从贵介绍有机水田里的菱角。

游客喜欢到田头吃一碗“割稻饭”。
和大陆一样,“三农”问题在台湾同样存在。上世纪70年代台湾工商业迅速发展,城市展现“磁吸”效应,人才、资金、建设重点涌向城市。二三十年过去,农村人口老化、建设停滞、失去生机。
重振乡村,一方面是实现社会的公平发展,还有更实际的作用:当城市里“钱淹脚目”的荣景不再,“新农村”建设可以吸引劳动力“上山下乡”,减轻城市的就业与人口压力。
10年1500亿新台币预算
台湾的“新农村”建设叫农村再生,《农村再生条例》规定1500亿元(新台币,下同)用于10年农村再生预算。这笔钱怎么花?不是自上而下规划工程、方案,而是自下而上申请。也就是由最基层单位农村社区(自然村)提出计划,层层上报县、市、“农委会”,如核准,便花到了这1500亿元。
什么样的申请会被批准呢?记者在台南市后壁区(县市合并前为乡,下同)长安社区、也就是林志玲的老家,被当地热情的大姐拉去看一个街头小公园,她说:“这原来是一个垃圾堆,要农村再生,村民提出把这里清干净,我们就提出申请,建了这个小花园。”这个小建设在外人看来真不起眼,但的确让长安社区的村民舒心了不少。
一位长跑农村的记者同行说:“这就是自下而上的好处,如果是自上而下,城里的长官或大学里的教授设计一个工程,却未必是村民想要的,甚至还与他们的生活习惯相抵触,与现实脱离,钱白花了。”
“这种方式没有缺陷吗?”记者问。“有!自下而上申请,工程批与不批,地方的政治人物发挥不小作用,可能会把批准与选票挂钩,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担心,还要观察。”
按农村再生条例,凡乡村的公共卫生、基础建设、文物保存都可申请再生资金。
成功的“无米乐”社区
“无米乐”取代了它原有的名字:菁寮,这缘于一部纪录电影《无米乐》,电影跟拍后壁区菁寮社区的种稻老农昆滨伯,记录他的生活、劳作与乐天:“虽然不知道台风、病虫害会不会来,随兴唱歌,心情放轻松,不要想太多,这叫做无米也乐啦!”
电影呈现的稻田风光和农家生活,点燃高度商业化的台湾社会的怀旧情怀,菁寮一夜成名。此时人们才发现,这个老旧的乡村深藏价值。在现代交通发展起来之前,这里曾是北上要道、集贸重镇,有店铺林立的嫁妆一条街,有印染、编织名产,有老教堂和百年历史的小学校,是台湾乡村一座活的博物馆。2007年,当时的台南县就在此实施农村再生,修缮嫁妆一条街上的连排二层木屋,恢复老的碾米厂、钟表铺、诊所、红砖三合院,这些工程不用来收门票,而是吸引艺术工作者和年轻人来此开店、办展,形成人、文、地、产、景的良性互动。
走在菁寮社区,你会看到电影里的昆滨伯当街卖米,文林伯牵着这个社区最后的一头水牛走过,也会看到络绎于途的城里人来此买米、吃“割稻饭”、逛老街、住民宿。菁寮社区的农村再生获了不少奖,是一个成功的再生典型。“他们的确有资源,这是再生成功的关键。”一位台湾同行说。
下乡的“知识青年”
有了人,有了年轻的知识人,乡村才不至于没落,否则投入多少钱都只会成为一时“政绩”。记者在台南走过几个乡村,大多仍然是老弱当家,寂寥冷清。在官田区遇到一位“知识青年”杨从贵,他说:“我的名字带着我的出身,爸爸从贵州来的。”他曾在IT产业任职,还有在苏州工作的经历,现在在官田办有机农场,种菱角、莲藕、茭白、稻米,并且联系附近采取有机耕作的农家成立“友善大地有机联盟”,建构自种自销自推广的链条。
官田乡村的标志一是菱角二是水雉,菱角是特产,水雉是一种美丽的水鸟,与水田共生。但随着农药的使用,水雉沦为“濒危”,引起台湾社会的重视,有机耕作水田成为农业主管部门推动的方向。“种有机田会饿死,如果你们没死,来找我。”杨从贵刚办有机农场时,村里的阿伯这样说。现在这位阿伯也是有机农,加入了他们的“联盟”。有机产量不高,卖相不好,如能生存下去,全靠消费者买账,靠“新良食”运动改变消费习惯。杨从贵说,他们的联盟不能再扩大了,因为产品会销不出去。
一进杨从贵的有机农场,他就打开投影机有声有色讲了一堂有机课,课堂门口放着“陪伴官田——2013认养计划”,上面标明各种有机作物的价格、汇款方式,把购买有机作物与认养土地的观念巧妙结合。记者回到台北后,又收到“联盟”的电子报,刊载“本周新品”,推广左邻右舍的“社区合购计划”,这些点点滴滴都是杨从贵的苦心经营,也是只有“知识青年”才能有的作为。
“你会买有机菜吗?”问一位台北的记者同行,“会,但有机菜不是到处有,而且不是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但碰到了会买。”
假设北京有像有机水菱农场这样的米、菜,有些贵,有些不好看,你会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