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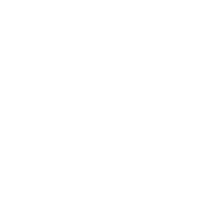

周思聪
一组《矿山图》,奠定了周思聪在中国二十世纪人物画界的成就,也成为走出徐蒋体系人物画转折的关键点,这样的评价早已在中国美术史中毋庸置疑。但最初计划由九幅作品组成的《矿山图》在完成四幅之后就没有再延续,80年代,周思聪对于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创作戛然而止,转向《彝族女子系列》和晚年的《荷花系列》。这样的转变正是关于周思聪个人艺术成就的争论焦点:在《矿工图》之后,这位才华横溢的女艺术家,其晚年的艺术成就究竟该如何定位?这样的转变有人肯定,有人非议。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非议者大多认为她晚年的绘画没有将《矿工图》这样的高峰作品延续下去,这是最大的遗憾;但肯定她晚年艺术成就的人却一致认为,后期的彝族人物画与荷花系列更符合周思聪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的真性情。
“对画家的作品有不同的评价,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正常的未必都是恰当的。彝族女子系列和荷花系列,不如《矿工图》那么有力度和影响,这很自然。但这样的比较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这是题材、主题、形式风格都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品。《矿工图》是她的转折性作品,是社会大转变时期的社会性主题创作。彝族女子系列和荷花系列,对周思聪也具有转折意义,使她的绘画达到了形式风格与画家内在个性的高度统一,即抒情风格与抒情气质的和谐。”郎绍君认为,更有内涵、更优美、更跟周思聪个性相统一的绘画还是后期的作品,尤其是晚年的荷花作品,她是用生命在作画。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作为周思聪近20年的学生,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这样总结她的艺术人生。那周思聪到底是一位怎样的艺术家?为何会从《矿工图》如此具有历史厚重感题材的绘画转向远离世事的淡泊风格?这似乎只能从她经历与性格追求中找到答案。
“有才气,绘画很独特,拿起笔画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郎绍君说周思聪的才气是卢沉自己都承认的:“卢沉比较理性,他一再说,就绘画才能论不如周思聪。不过,他读书思考,在思想观念上对周思聪有一定影响。”天生的绘画才气加上央美附中和本科严格的绘画功底和造型能力训练,让周思聪的绘画在同辈艺术家中显得更为出色。
聊到周思聪个人性格时,王明明这样形容自己的老师:“话不多,非常善良,为人好,但内心骨子里有非常强的个性。”郎绍君则这样形容:“卢沉直率热情,十分健谈,非常关注思潮与理论,周思聪话不多,声音轻轻的,但有实在的见解和态度。她曾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多说话都能彼此了解,是真朋友。我比较注意他们的画,他们比较注意我的文章。”他也认为周思聪外表柔弱,但内里却有一种骨气。
都说有才的人都是孤独的,甚至连老天都会嫉妒。周思聪就是一个让老天都嫉妒的才女,所以从年轻时她就很劳苦。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院之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文革开始之后,周思聪就与广大画家一样,被政治和艺术的矛盾困扰着。1969年与卢沉结婚,在丈夫下放外地的境况中,她承担起了家庭的负担。直至文革结束之后,作为画家的周思聪才体验到了解放的感觉,也就是那几年里,进入了她创作的高峰期,《人民和总理》《矿工图》的部分组画都是那段时间完成的,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太长久。
从早年间,周思聪的父亲生病需要照顾,卢沉的母亲也跟他们一起生活,善于艺术研究的卢沉对家里的事情并不在行,两个孩子还很小,家庭大小事务都由周思聪一人承担,她总是无论冬夏在冬天院子里用冷水洗衣服,这也似乎是她后期得类风湿病的原因之一。随着卢沉患肝炎,周思聪开始负担起了更为艰辛的家庭和精神负担。但是话语不多的周思聪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很少有表露,不久之后周思聪得类风湿关节炎。这是《矿工图》没有完成的最直接原因。

《矿工图之五——同胞、汉奸和狗》 周思聪178cmX318cm 1980年
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在撰写“大爱悲歌”展览文章《悲天悯人——对<矿工图>组画的思考》时,具体考证了周思聪当时的处境,周思聪给好友马文蔚的信中有这样几个片段:“卢沉因病不能画,我的压力很大。这画要表现一种力,需要有男人的气概,我感到自己还缺少这力量。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曾经是那么希望着,共同完成。他毫无道理的冷漠,伤了我的心。”吴洪亮认为,作为女人、作为妻子、作为合作伙伴周思聪对此是有些怨恨的。
卢沉退出创作,周思聪病情加重,《矿工图》最终还是没有继续下去。“类风湿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无休止的疼痛,关节变形,伤口难以癒合;不断的住院、治疗,无法解脱的烦脑,组画就搁置了。严格说,她的风湿病痛,有一段是时好时不好,不是完全没有接续画的可能。我问过她,除了病痛,还有没别的原因?她说:就感觉自己力度不够。我在《心欲静,忧未歇》一文中说:这‘力度’不是尺幅和笔墨形式方面的,大约是心理上的。作品挽救的历史苦难及其惊心动魄性,需要画家巨大的意志与承受力量。周思聪太多柔肠,太多同情心,她似乎难以忍受从自己笔端流湍出那么深广的痛苦。她认可我的这一推想。实际上,她放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时候,除了身体与心理,还有家庭负担的压力,以及艺术上的另一种追求。”郎绍君说,在创作《矿工图》的期间,1981年周思聪到四川大凉山访问,彝族妇女的形象和生活状态使她深受触动。
绘画里投射的自我
从文革时期到《矿山图》,周思聪的人物画创作一直承载着艺术家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但当她到了彝族地区之后,她说:“在那里我看到的、感到的和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里地球转的特别慢,人们自生自灭,像植物一样,他们没有文化,但人与人之间却很干净,比较原始,这就很入画。”
郎绍君觉得周思聪找到了符合她内心想要画和想要表现的对象,“她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慰藉,一种相对宁静、平和的心态,不想再激烈的宣泄,再承载过于沉重的社会主题了。”《彝族女子系列》创作是她一种艺术风格和意趣的一次转化,是对身体、家庭多重重负感的慰藉。
“卢老师是一个非常大度的人,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是一个粗线条的人。他丝毫没有发现他的妻子是那么感情细腻和细致,在精神世界有一种特殊性,需要沟通,需要安慰。所以周老师找到了一个好朋友,把她从来都不愿意说的心理话以书信的形式告诉她的好友马文蔚。”王明明感慨。
周思聪性格里还有一种敏感的一面,尤其是对人生悲哀的的情感特别敏感,所以她所感受到的彝族是安静、质朴、没有任何激烈的矛盾、时间甚至是静止的,这与大部分去到彝族地区的人们感受到的并不相同,大部分艺术家对于彝族的印象多以能歌善舞、火把节、宗教仪式等欢乐为主,但周思聪的关注点却在彝族人普通、真实又劳苦的生活,所以周思聪的感情是细腻的,她也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她所看到的彝族风情,在她笔下的彝族妇女平静、忧淡,却也总是辛苦的背负着重担。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1981年
“她从大凉山归来的第一幅重要作品,刻画了两个在背柴途中歇息的彝族妇女,题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正是她的感受和想像——没有争斗和混乱,只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简朴生活。周思聪是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她所看到的彝族女子,她们贫穷,勤劳,淡然、朴素。画她们的笔线和色调也是恬淡抒情的。”郎绍君曾经撰文说这件作品还延续着《矿工图》的浓重陈郁,却没有了《矿工图》的解列和悲怆,“画中两位在途中喘息的彝族妇女,脸上雕刻着沧桑、眼神却木然、漠然。”
周思聪在90年代《江苏画刊》的访谈录里说:“我到了那里就有一种共鸣,好像在上一个世纪的梦中曾经想见,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融洽。”到1983年,周思聪完成了一批彝族女子系列作品包括《高原暮归》、《边城小市》、《母女》等作品,已经和第一幅彝族绘画有很大区别,郎绍君认为:“这些作品笔墨风格已经不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凝重,空间也变得开阔起来;人物精神的‘淡’则依旧:无论她们在做什么,都像无所谓,无所注意似的,但又很自然,没有一丝牵强。我曾注意到在这些作品中较多出现的妇女形象。她们‘多孤独一人,或在秋雨里、或在雪夜中,或在草地上,身处空阔的原野,云天低垂,尘路漫漫,独立移步,艰难而无怨’。”

《高原暮归》
表面看来,在美术史地位上,周思聪后期作品的确不如《矿工图》的地位,但是却开始符合她的真性情。“从《矿工图》人物的激厉、悲愤、转而为这样简淡而美的彝族女子系列,表达出画家历经‘文革’苦难后,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求和想像。作品的风格与画家内在世界和谐是不同于《矿工图》的艺术境界。”郎绍君这样评价她的《彝族女子系列》。
痛苦伴随的精神升华
即使生活并不太顺,但周思聪与丈夫卢沉在艺术上的志趣一直是相同的,即使各有侧重和所长,但却也相辅相成。卢沉的主要成就在中国画教学上,周思聪同样也影响了80、90年代的不少年轻人。
“80年代中期,中央美院国画系开人体课,请周思聪去授课。她和学生一起作画,用圆珠笔勾画了一批巴掌大小人体画,这批人体的特点就是‘变形’。课堂上画人体,一般都是为了解决结构、色彩、光线等技术性问题,但周思聪看到和追求的不只是这些,她关注的是生命苍桑在体形上留下的痕迹。这样,在写实性追求的同时,她适当用了一些夸张手法,把那种苍桑感突显出来。这体现出画家的对生命特别是对女性生命的敏感,这种敏感与《矿工图》的表现主义物质有某种联系,也与周思聪的女性艺术直觉分不开。这批小画传到各地,不自觉的颠覆了人体画单纯的技术目的,以及单纯的唯美追求,人们竟相摹仿,对当时方兴未艾的人体绘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郎绍君说周思聪画的人体,有生动的肉体,更有深层的精神追求,只是可惜这批作品大都在学生间散出去了,没能够完整的保留下来。
王明明深切懂得周思聪的教学方式:“从72年跟着周老师学画,一直到她去世。早年跟她和卢老师去煤矿采风,学画。到后来她调我到画院,我慢慢意识到两位老师的教学方式,在绘画上必须跟老师保持一定距离,他们也不限制我,只要是好的他们也都会接受,只要你有才气,他们都完全放开,看到画的好的学生他们总是如获至宝,两个人挂起来看,到处推荐。很多人都得到过他们的提携、赏识和鼓励,他们是真正的教育家。周老师不爱多说话,可说的我记住了总是受益终生。”
但是这两位难得的艺术家和教育家却并没有得到太多命运的眷顾。随着病情的加重,周思聪后来已经不太容易继续进行人物画创作。荷花,是她80年代后期开始,集中于病重之后的90年代创作的。

《荷花》 54cmx98cm
“多年的病痛,不断的住院、打针、治疗,朋友们帮助她到新加坡、美国治疗,也未能明显好转。久不离病榻,她渴望重返大自然。在帅府院的家里,在北京第六医院的病房里,我都见过她用变了形的指关节把笔画荷,画风雨小屋,山水小景。物质生命的困境迫使她寻求精神生命的寄托。笔力和气势不够,就追求墨色和韵味,花少叶多,晴少雨多,没有‘红莲沉醉白莲酣’的盛景,不乏‘月白风清欲坠时’的忧寂。浮萍淡如泪痕,残荷恍似乱云,折落纷披,仍透着生机。寂寞中不乏热情,愁思中又交织着喜悦。前人画荷多‘出污泥而不染’的隐喻,周思聪画荷则直抒心曲,深情动人。”郎绍君说荷花从另一个方面突显出她的杰出绘画才能。
北京画院专门研究周思聪的研究者薛良告诉记者,了解周思聪越深入的人,总会在周思聪的精神世界里陷得越深。的确如此,了解周思聪的人似乎很容易被她吸引,而对于这批荷花作品,王明明说只能从精神层面去理解,其他方式都无法解读。

《朝露图》 69cm×46cm
“周老师那时身体的状态,所承受的痛苦,对她是一种精神升华,她跟我说过,说都想通了,一切随缘。”这就是王明明为周思聪所总结的“归于平淡”,他说周思聪最后一批荷花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无”,技法上减到了不能再减,就像是一种解脱和精神的蜕变,周思聪并不信佛,却像是到了佛学中的最高境界,画中的空灵恰好与她的精神是巧合的。
“从对命运的抗争,到后来的无奈,再到最后的解脱,这是周老师精神上的领悟,把自己的痛苦全部放掉,顺其自然。”对于周思聪晚年的艺术道路,王明明这样诠释。

《洗尽铅华》 宣纸·水墨54cmX49cm 1992年
臧伯良回忆周思聪
前一段时间在整理李可染遗体告别的录像带时,看到了很多画家,这些画家二十年后已有很多已不在世,其中就有新中国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画家、人物画大师周思聪、卢沉夫妇,周思聪是继即中国近现代史上任伯年、蒋兆和之后著名的人物画大师,她继承了她的老师蒋兆和的中国画传统,周思聪完全没有旧的东西,她在新的时代,推动了中国人物画,往前大大的走了一步。周思聪70—80年代的作品,吸收了油画及素描的体块结构、明暗光线,又大胆的运用了大面积的水墨晕染,把李可染先生山水画的层层叠加技法,运用到人物画的创作中,开创了一代中国画的新面貌,真正是新时代中国画最杰出的人物画大师。
记得1980年的春节,好像是初三,在李可染家里碰到了周思聪,那时周思聪还很年轻,四十左右,她原来是中央美术学院蒋兆和大师人物班的学生,并不是山水班的学生,但她崇拜李可染先生的人品、画品,一直把自己称作是李可染的学生,自从那次相识之后就经常去她家中请教或是能帮他做点什么,三十年前,周思聪住在北京光华路附近,那时候光华路(即东三环,老中央工艺美院对面)还荒芜的很,印象中周思聪是住在六层还是四层,记不清楚了,房间很小,大约也就五、六十平米,卢沉先生是他的丈夫,当时不怎么在家住,周思聪带着孩子、屋里乱糟糟的,好像根本下不去脚,不能想象,周思聪怎么在这间屋子里画画,当时的北京画院还在地安门附近,是个大四合院,也很挤,根本没地方画画,周思聪家楼下一楼还住着一位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弟子,以画虎著称的胡爽庵先生。
大约是在1986年前后,周思聪、卢沉搬到了老中央美院(王府井大街帅府园),那是一个新盖的红砖六层楼,好像是在三楼,80年代,因为在南方开着画廊,主要以卖自己的画为主,还卖些国内名家的作品,当时周思聪、卢沉的画,四尺三裁的,在荣宝斋也就是百八十块钱,她虽然是一代大画家,可她总是窘窘的像个家庭妇女,臧伯良曾经帮她卖过一些画,记得1985年初,给她结了一笔账,大概卖了七、八张,每次都多给她点润笔,一共800块钱,又给她留了一千块,当时一千块可以拿到周思聪十张画,那个时候,她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病魔折磨得她脸色土灰,她说:“我这个屋子特别乱,根本没法给你画,干脆你就拿一些我参加展览的画吧。”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北京女画家联展,展出了她三十几张画,都不太大,都是四尺三裁的和四尺对开的居多,当时她的画风正由写意的人物往变形上过度,那个时候她刚刚拿出了一批彝族少女为主的作品,画的非常精致,线条肯定,结构清晰,脸部还有她以往的傣家少女的风格,非常雅致、漂亮,臧伯良当时连忙推脱:“不不不,这些画是您参展作品,也是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卖了就实在太可惜了,您还是随手画一些以前傣族少女的老风格的作品吧……”
至今记得她眼中透着不解和有些惶恐,她右手收起画,左手急急的去拿那一千块钱,仿佛是臧伯良要拿回那一摞钱,当时没有一百元人民币的面额,那一千块钱很厚的一摞,她似乎感觉臧伯良不想要这批画,想想,都心酸得想掉眼泪,臧伯良一生都不会忘记周大姐那种期许的目光,臧伯良说:“不不不,周大姐这个钱你先用。”大家知道那个年代生活很拮据,她跟卢沉大哥两个人的工资才100多块钱,她身体那么不好,非常需要营养,她和孩子也需要添些衣服,她总是穿着旧旧的衣服,像个家庭妇女,又聊了一会儿,周大姐仿佛很不安,好像她不愿意白拿别人的钱,她非常希望臧伯良能高高兴兴的拿走一些作品,臧伯良心里非常难过的跟她说:“大姐不着急,这十张画,我以后再来拿。”从此以后,她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王明明我们既是亲戚又是好朋友,他是周思聪的大弟子,所以有什么事,就问明明,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曾经在画展和公开场合见到过周大姐,周大姐总是说:“有时间你到我那儿去取画……”可是看到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在公开场合我们相遇的时候,她总是主动跟你打招呼,把你拉到一边,这时候,反而更加非常不好意思,大约是在1987年左右,有一次画展上我们碰到一起,握手时,她的手直直的各个关节都肿的像个木头棒子而且冰凉,臧伯良非常惊愕的问她:“周大姐,你身体怎么这样啊?”她也很难过,没说什么……
1989年12月5号,我们的恩师李可染先生去世,治丧期间她去了可染先生家有四、五次之多,那个时候看到她身体更加的每况愈下,连走路都气喘吁吁的,到李可染先生去世的时候,已经靠药物维持,从此以后,到她去世,再也没有去过她家,因为她那种窘窘的期许的眼神,让人异常难过,想过再去她家,给她送点钱去,但想想她一定不会要,她还会提起前面那十张画的事,从1986年离开她家,就听王明明说她根本不能画画……
周思聪一位新中国培养的女画家,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画家,苍天就这样折磨她,57岁便离开了人世,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女画家,走过了她57年的短短的艺术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