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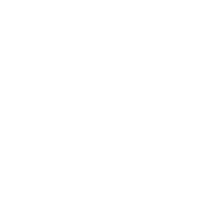
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洋洋百余万言,谈到了许多国家,如美国军事上的强大,英国式的民主,意大利法西斯的兴起,北欧各国的福利,等等,但谈得最多的还是日本。他对日本的看法既富有对历史回望时散发出的沉重,又充满着面对现实时因企盼中日友好而萌生的放心不下。由于他对日本的看法来自于他和日本的直接接触和长期思索,因此,他的回望是有分量的,他的放心不下是值得沉思的。
政治极端:可怕
在张学良眼里,日本是一个政治极端的国家。国民对天皇的崇拜极端,一人统驭万民;军部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极端,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军人控制国家政治的手段极端,暗杀如家常便饭;训练国民的方法极端,“日本没有老百姓,全是军人”。这些看似感性的看法,实际上含有一定的法理层面的认知。
“根据法律,天皇是陆海空军大元帅。”“那时候的天皇他有力量。”张学良所说的法律,是指日本于1889年制定的明治宪法。明治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和巩固了近代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专制政体。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统帅陆海军”。天皇的权威具有绝对的至上性,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外交等无所不包。所以,张学良说“那时候的天皇他有力量”,力量大到一切权力独揽。“天皇制是一种机构,是绝对主义的国家机构。”绝对的国家机构必然导致国家政治的极端化。以明治宪法为标志,近代日本极端的政治结构和极端的伦理结构完成了体制化和法制化,为日后日本走向各种极端奠定了制度基础。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提到天皇的话只有这么几句,但这几句话是他对日本看法的核心理念,他对日本的其他看法都以此为中心而展开。
在天皇专制政体中,天皇的军事统帅权尤为突出,国家军队由天皇统帅,这不仅确立了天皇是日本最高军事独裁者、军队非国家化,也确立了军人在国家中的特殊地位。由于具体指挥军队的军部直接对天皇负责,军部也逐渐获得了次生的独裁地位,享有在国家决策中明显高于其他政府各部门的特权。张学良说:“那时候,日本的军人在宪法上的权力太大了”,“根据法律……陆军参谋总长可以不经过政府,有直接上奏权,内阁不能问”。天皇的最高统帅权与军部的特权上下结合构成了近代日本极端的军事专制政体。在这种体制下,军人的权力急剧膨胀,一直膨胀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都被军人所控制的程度。张学良感叹:“日本,到我说的那个时代,无论什么人组阁,如果军人不同意,那内阁组不成。”
张学良与日本接触最多的时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而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国家政治在军人的操纵下走向登峰造极的时期。对外,扩张加剧,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发展到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对内,推行“铁血”政治,血腥镇压反战力量,对不同政见者实施恐怖暗杀。1927年4月,日本军阀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内政形态进入恐怖化阶段。“日本陆军部的人事局局长也是一个中将……他在他办公的屋子(里),一个日本的中校,拿出剑来把他刺死了。……日本军人狂妄到什么程度,他(是)很有地位的人,等于咱们国防部一个次长一样。这个人很好,很稳健的。大概也是与中日关系有关系。”“他把自己的长官都给杀了……那你还说什么?他对国内如此,那对国外他想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日本军人的狂妄将日本极端政治的残酷性发展到极至,对内部不同政见者的恐怖,对邻国的凌辱,内外两条线平行恣肆、互相映衬、内外相促,使日本政治的极端性统一于一个整体,发展到了极限。
随着军人在国家中地位的上升,日本军队的数量直线上升,庞大的军事开支超出了国家所能负担的能力。20世纪20年代末,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日本也遭遇“昭和恐慌”。时任内阁陆相的宇垣一成,顺势以裁军为名,实行“以质量换数量”的假裁军,组织退伍军人训练在校学生及社会青年,将日本引向了社会控制军事化的“总体战”体制。张学良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日本没有老百姓,都是军人,到了年龄就是预备军人,往上去就征兵到了军队了,到军队当上两年,下来以后就叫后备军人。从预备军人开始时就受军人训练了,所以日本(国民)都是军人。”“整个国民都在军人手里。”宇垣裁军实际上是日本政体走向军事独裁化的重要步骤。
在一般人眼里,人们看到的是: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仅用不到50年的时间,就在世界的东方堆砌起了一个足以威胁整个亚洲的金字塔帝国,整座金字塔放射出一种刺眼的、令人生畏的极端色彩。张学良透过高耸的塔身和极端的色彩,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内部结构,敏锐地发现,这座金字塔的塔尖是至高无上的天皇,塔基是已经军事化的国民,塔身是一群狂妄的军人,并看到整座金字塔被一部扭曲了的宪法紧箍着。由于极端被宪法包装着,既增强了其结构的稳固性,又增强了其欺骗性,致使其耸而不折,极而不散。
军人狂妄:可恨
在近代西方工业化大潮冲击下,一些日本政治家对本国地理、资源上的自卑情绪演变成急于改变劣势的自补自救的心理,而自补自救心理的超常膨胀,催生出自补式的内部“强军”和外补式掠夺的疯狂。两种疯狂给日本带来的物质上的“狂喜”,诱发原有政治理念上的极端像癌细胞一样发生裂变,并迅速扩散到整个国家机体。国家机体的变化首先使国家机器变成了战争的发动机,日本的独裁者在隆隆作响的战争马达声中,彻底失去了理性。在失去理性的政权操纵下,军人将对内恐怖扩展和放大到整个占领区域,其野蛮性暴露无遗。
日俄战争之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东清铁路以长春宽城子站为界,以南的铁路划归日本,改称为南满铁路。从此,中国人不能过南满铁路,“抓住你,就把你塞到火车里,给你烧死”。等地方政府和日本人办好交涉手续,领人时,“他们已经死了”,“连个尸首都找不到啊。不但军人,连老百姓也不能过南满路,抓了就扔火车炉子里给烧了”。“铁路沿线30里都不允许中国人接近。”南满铁路如同穿行在东北大地上的“蛇形王国”,专门吞噬中国人血汗。
“蛇形王国”再毒,总还有一个长度和宽度,中国人“不能靠近,还可以躲”,而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中规定日本人在东北有商租权、杂居权,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做顾问,这比“蛇形王国”更加恶毒。“我年轻时吐血,身体不好,有病。”“我当时很悲观吶,不但对我自己的事情悲观,东北呀,二十一条啊。”
“二十一条”何以对张学良刺激如此之深?张作霖顾问町野武马在《炸死张作霖前后》一文中说:“二十一条”签订后,日本政府“给我一个训令:‘发生战争时,俘虏张锡鉴’”。张锡鉴当时是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为了在战争发生的第一时间内俘虏张,训令要求:“贵官应该搬进张锡鉴家。”张问:“你是来干什么的?”“一交战,我就要俘虏你。”町野在中国做了14年顾问,给张作霖做了11年,町野自己说,张作霖身边的人“目睹我有如张作霖之头子”。日本顾问町野是这样,土肥原也是这样。一提起土肥原,张学良愤恨不已:“他这个家伙坏透了。”“我后来跟他闹翻了,他说你没有换我的权力。我是没换他的权力,但是我有不跟他说话的权力吧!我当着特务长官的面,告诉我的门房说,土肥原顾问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我不见。”
日本顾问是日本以强凌弱的缩影,张学良通过日本顾问的所作所为更加看清了日本的强盗本质。
一个国家在别国的土地上采取恐怖袭击的手段炸死该国最高领导级人物,这不仅仅是不聪明之举,实在是野蛮到了极点。而张学良只说是不聪明、看事情狭窄,这恐怕是只有千年文明大国熏陶出来的人才有的超级雅量和胸怀。但这绝不是张学良的糊涂和懦弱,而是一种清醒和坚强。张学良认为日本炸死他父亲,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岛国因无法理解一个大国国情所作出的错误判断而采取的极端恐怖;是一个强盗国家依据已经过时的“行抢”经验炮制出来的愚蠢。日本要在中国寻找傀儡,对傀儡的第一要求是唯日本是从,不从则杀。“日本那些少壮派的人感觉我父亲不听话,不给他做傀儡。”“日本人那时很糊涂,太笨,我父亲那时也是一心想合作,但你这个合作条件太苛刻。”日本人认为炸死了张作霖,东北就归张学良了,张学良年轻好摆弄。“我说日本人不聪明……你把我父亲炸死了,国家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跟你合作?……所以我认为日本人把事情看得很狭窄。”日本以为中国还是甲午战争时的中国,没有看到中国人正在觉醒。“日本完全把中国判断错误了,我跟日本人说,你们完全把中国那个时代的人看得好像是倒退50年、100年那时候,好像吓唬前清时那些人,中国人那时候都差不多觉醒了,我说日本对中国的形势没弄清楚。”
1927年4月,田中内阁成立,明确提出“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实施对中国步步紧逼政策。“那时我跟日本人说,我们情愿当个小兄弟,那都不行啊!”“日本文人拿不到太大权,日本军人实在不懂外交政治。”“那时南满铁路、旅大到期了,因为交还,我们事前去谈一谈这个事情。我当时就划一个政策……主权是我中国的,我收回。”“结果他们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他说,我们日本有句古话‘城是箭射来的,你要用箭射回去’,这意思就是我武力拿来的,你说那些条件都没有用,你也要用武力拿回去。”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失去理性,国必亡。张学良既是日本失去理性的目击者,也是受害人。因此,他在晚年,用宗教式的语言发出感叹:“日本这个国家没有亡啊,真是上帝的恩典!”
军事先进:可师
杀父仇人前来“祭吊”时,张学良曾萌生将其击毙,用仇人头颅祭奠父亲的念头,“后来明白我不应该这么做……报仇也不是这么个报法”。这说明,张学良虽处血气方刚之年,对日本仍保持政治理性,徐图彻底解决之法。什么是彻底解决之法呢?看到日本的进步,以敌为师,壮大自己。
徐图彻底解决之法的努力之一:利用日本政坛的矛盾,对有可能改变政局的实力派人物施加影响,利用独裁政权普遍存在的“政随人转”、人亡政息的特点,努力使日本政坛发生对我有利的人事变化。这一努力本来是悄悄进行的,被日本发现源于一张“收条”。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占领了大帅府,日本军人狂喜异常,但在打开张学良保险柜的那一刹那,日本人由喜而惊,由惊而辱,由辱而惧。原来,“他们把铁柜打开了。我那铁柜里藏着两件事情,一个是那洋钱(枪杀杨宇霆、常荫槐前算卦用过的银元),另外一个,有一个叫床次的,日本的一个政党的首领,他要回去竞选首相……他竞选用钱。当时我就给他50万……所以那个里头有他一个收条”。日本人看到“收条”,倒吸一口冷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位刚及而立之年的“少帅”已把抵抗的触角伸向了日本政坛,更没想到竞选日本内阁首相的政党将求援之手伸向了张学良。
1921年秋,张学良奉张作霖之命访问了日本,这是他第一次踏出国门。他在日本参观了一个多月,“因为我种种接触,使我感觉到日本图谋中国之险恶之深远,令人不寒而栗。同时,我也认识了日本之国力,中国若不甘愿作奴隶,必须奋起图强,决不是空言可以抵御日本之侵略的”。为了抵御日本,他和近代许多中国人一样,萌生了“以敌为师”的想法,他想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因为他在参观中“十分崇拜日本军事教育”。归国后,因战事紧张,东渡日本学习一事没有实现。但他向张作霖建议,以敌为师,整军精武。张作霖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奉天空军就由日本训练了,也买了日本飞机”,另外,选派年轻军官赴日留学。他执政后,被他提拔的著名军官中有50多人是留日的。如东北边防军宪兵司令、陆军中将陈兴亚,北平行营参谋长、陆军中将戢翼翘,第六十七军中将军长吴克仁,第五十七军中将军长何柱国等。
很显然,在情感上,张学良处于对日本既憎恨又羡慕的双重构造中。“我根本恨透了日本人。”“恨是恨,人家是真厉害。”从情感上,他无法摆脱对日本的厌恶和憎恨。但是,张学良日本观的理性在于,他对中日两国实力的认识并没有因杀父之仇而扭曲,没有因遭受凌辱而不加区分地对日本一概排斥,他不仅把日本文人与武人、商人与政客、极端的上层与盲目的下层、侵略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作适度区分,也把日本经济上的成功、军事上的强大与野蛮黑暗的一面区分开来,清醒地认识到,中日国运之不同、国与国关系之不正常,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源于两国实力的悬殊。当时分裂的中国、软弱的中国受日本军国主义欺侮的命运是难以避免的,改变这种命运的唯一方法是使自己强盛起来。怎样快速强盛?不能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而排斥向日本学习。“以敌为师”固然是痛苦的无奈,但又是深刻的理性;憎恶强者对弱者的轻蔑和欺侮是自然的,但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弱者自身缺陷的反省和弥补的努力。张学良对日本的憎恶与效法,不是盲目的诅咒与称羡,他的终极关怀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是对自己祖国和同胞深沉的爱。
祭祀战犯:宜防
由于近代日本给中华民族留下的伤痕太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张学良又是受害最深者之一,因此,张学良直到晚年,一直在关注着日本。当他沉默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开口说话时,已是91岁高龄的老人。此时的他已把一切都看得云淡风轻,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中日两国的未来。为了未来,他对日本的年轻一代提出了忠告。
忠告之一:不要用武力侵略别人,那等于“自吞炸弹”。“日本投降了,那我心里很安定,我没有什么。”没有了“仇”,也已经忘却了“恨”。“谁能让(日本)变成原子弹实验场,死了那么多人,谁招的呢?自己招的。……做人哪,就是本着良心,问心无愧。”人的良知一旦泯灭,离毁灭也就不远了。如果你以武力侵略别人,以强凌弱,“你早晚会惹出祸来的”。日本惹出的祸,“九一八是开头。所以日本元老西园寺也承认,日本等于吞了一颗炸弹”。
张学良的认知,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的“不要用武力侵略别人”的忠告是他的忠告,也是历史的忠告。
忠告之二:不要以经济侵略别人,只要是侵略必然会遭致反抗。“如果你要经济侵略,别人也不是傻瓜,你将来还是会遭到反抗。”91岁这年,“我跟日本人说,我说你用这经济侵略,你知道将来的后果,是一样的后果。你怎么不反过来经济合作呢?”“要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对弱者帮助,弱者强大后也会帮助你。”
忠告之三:不要忘记历史的罪错,“忠”而不“恕”,是一种极端。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不仅富有沧桑感和沉甸甸的历史厚重,更富有人性化的恳切与博大。“我和日本NHK谈话,我说中国有句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是我执行这事我尽力,恕道是我能原谅人。日本人是忠烈极点,没有恕道。”张学良认为中日两国文化同源,之所以日本走向极端,就是日本把“忠”发展到了极致,“日本人的忠是世界第一啊,武士道嘛。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那样”。“日本现在解除武装,不让它搞,一旦它恢复,它还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日本把他们10个人(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笔者注)都入到那个靖国神社”,“日本的事情都是他们几个惹的。”“他们这10个人入靖国神社,可以看得出来,日本还是一个侵略国家。”
“我只说了事实,让别人了解。我的看法对错,这是另外的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能否真正的复活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也可能日本极右势力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梦想会被日益强大的国际正义力量所挤碎,不过,不管“日本还是一个侵略国家”的判断是对还是错,将战犯移入靖国神社供人参拜,必然使得日本人的历史观和战争观发生模糊和混乱,同时也会给极端思潮的泛滥提供温床。错误的历史观、战争观一旦同极端的民族主义纠结在一起,即使历史不会重演,也会严重地伤害中国人民及亚洲人民的感情,值得警惕。
张学良的一生,深刻地经历和体验了身为弱国军人的屈辱和愤怒,近代日本给他和他同时代的人造成的心灵创伤,是和平时代的人无法理解的。因而,从横向上说,他对日本国家的极端性、日本军人的野蛮性的认识要比一般人强烈得多。同时,他又在比较中看到了日本的长处,日本的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先进的军事装备令他羡慕,他也悄悄地效法过,一度也产生过恐日的心理。这种憎恨与佩服、畏惧与效法的相互交织,构成了张学良对日本看法的矛盾性特征。从纵向来看,以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以旅欧归来为界限,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前期以恨日、恐日、师日相互交集,后期以强烈的抗日为主线,晚年提出防日的忠告。
总的来说,在张学良同时代人中,很少有哪个人的日本观是如此的客观而完整、真切而深刻。说他的日本观客观,因为一甲子多的时间已经平复了他的昔日之恨;说他的日本观完整,因为这位世纪老人到了晚年还在密切关注着日本发生的一切,而且这种关注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感性、理性、人性,民族的特性、历史的惯性、文化的传承性……说他的日本观真切,因为他对日本的每一个看法都缘于大量的、带血的事实,而且这些事实不是他亲耳所闻,就是亲眼所见,更多的是亲身经历;说他的日本观深刻,因为他对日本关注时间之长、对日本观察之细、对日本了解之深皆有过于常人。